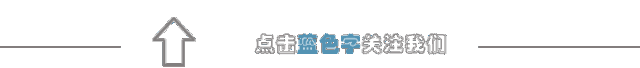


福贵的吝啬,在寨子里是出了名的。
福贵和黄牛水牛骡马牲口打了半辈子交道,除了咒骂那些畜牲外,一句多余话都不愿说。就连出门干活,上桌吃饭,端杯喝酒,添锤打架,永远只用一个字来表达:
甩——!
短短一个字,配上他的表情手势,再加上当时的环境氛围,所有该表达的意思都显露无遗。
福贵的吝啬,还跟他另一个习惯有关。吃完饭,福贵总喜欢倒上半碗素汤,哗啦哗啦,把碗涮净了喝下去,连半颗油星子也不会拉下。一说起福贵,周围的人都会骂他:那个龟儿的,屙尿都要用棕滤过,生怕把金子漏掉了!

大集体的时候,福贵是生产队的饲养员,专门负责队上的那几十头牛。可是,福贵不甘心困死在牛圈房里,经常偷偷摸摸干些投机倒把的勾当。福贵把东边集镇上的鸡仔背到西边集镇上,再把西边集镇上的猪娃转运到南边市场,钱没有赚到几个,却被抓了几次现行,让他斯文扫地。福贵挨过几场批斗,没有伤筋动骨,但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,头发被揪掉了好几撮,逢人更是轻易不肯说半句话。
福贵一身的坏名声,在土地下户后却派上了用场。福贵专做贩牛生意,在乡下低价买了牛,再贩到成都、昆明等城市当菜牛,从中赚些辛苦钱。
按理说,福贵踏踏实实做小本生意,不招谁不惹谁,偏偏就有人对福贵冷眼相对。
对福贵愤愤不平的人,都是他熟悉的乡邻。说穿了,是因为眼热他腰包里那几个钱。
修房子要钱,娃娃读书要钱,老人生病住院要钱。地球人都知道,福贵贩牛赚了不少票子,于是,大伙儿都编着各种动听的理由,期望把福贵的钱借出来。
福贵呢,不管别人的话说得多么动听,那只手把腰包捂得紧紧的,轻易不会答应借出去一分半文。福贵不仅背上了一个老吝鬼的名号,家里的鸡、狗、猫会莫名地死掉,屋顶上的瓦也经常在夜里被从天而降的石头砸出一些窟窿。

福贵倒也大度,从来不会去追问这些事情的根由,专心去做他的贩牛生意。
福贵把钱捏得紧,只有福贵自己知道,那几个钱来得实在不容易。
一旦出远门,福贵就会带着他的哑巴侄子,身上背着四五十斤东西:一半是牛的饲料,一半是自己的口粮。到了傍晚,牛困人乏,在稀疏的夕阳下,还得用谦卑为这一天的辛劳画上句号。借人家的院子把牛关好,借人家的锅灶生火做饭,还得买些干草料让那些畜牲打发夜里漫长的光阴。
风餐露宿,饱一顿饥一顿不说,要是遇上价格波动,老本都会赔一大截进去。
这两年就是这样,成都的行情不好,福贵就专往昆明跑。
这一天,他们过了元谋,在一个叫打狗凹的村子歇脚。村头有一户人家,空屋子多,院子也宽敞,正好用来关牛。遗憾的是,男人去缅甸做生意,三年多了还没有音信。屋里就一个女人,供养着呆痴痴的婆婆,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娃娃。里里外外靠女人那双手,苦涩的日子里让孤寂塞得满满的。
“又来了咯!”
福贵赶着牛才出现在门口,女人脸上就飞出一片红晕,一口细碎的白牙呢哝出吟吟的笑意,眼睛里满是灵动的光。
福贵没有应声,用浓重的鼻音打着招呼。
女人手脚麻利,帮着哑巴把牛关进院子,飞快到地里拔了两棵菜,扯了两个瓜,就在厨房里帮着生火做饭。

福贵成了闲人,坐在院子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。傍晚的太阳很温柔,淡淡的霞光把远山烧得红红的,清凉的夜风撩拨着福贵的神经,痒痒的,麻麻的,让他感到特别的舒爽。
女人把热腾腾的饭菜摆在桌上,东边山凹上的明月已经高高地升了起来。
“饿了吧!”
“嗯!”
“吃得惯不?”
“嗯。”

“赶了一天的路,多吃点!”
“嗯。”
月影细细地筛落在院子外面的树林里,小虫子的吟唱犹如一只酥麻麻的小手,挠得朦胧的夜色昏昏欲睡。
女人收拾好碗筷,打发两个孩子睡下,烧好一锅洗脚水,走的时候犹犹豫豫丢下一句话:
“那边,门没关……”
女人的声音很小,一下就被屋外小虫子密密实实的欢叫给吞没了。福贵没有说话,嗓子里好像有无数条蜈蚣在爬,背上也出了一层细汗,胸脯像安了一台风箱。半个多月在外面晃,福贵眼睛里的火苗蹭蹭地直往外窜。
走的那晚,家里的媳妇极尽缠绵,到现在还能嗅到淡淡的体香。他明白媳妇的用意,担心他在外面打野食。
福贵抽着旱烟。哑巴自己到小楼上睡了,空阔的厢房里就留下了福贵。清清的夜风,唧唧的小虫,以及那扇虚掩的门福贵烟,撩拨着福贵兴奋的神经。福贵长叹一口气,使劲做了两下干咽的动作,犹如吞下一堆欲望。福贵老是觉得床硌得身子疼,劳累了一天,就是睡不着。
半夜,起了风。几声闷雷过后,门响了,女人飘然而至。
“好怕!”
女人欲言又止,眼里满是哀怨。三年了,男人一直没回来,地里的收成不好,日子过得艰难。
福贵翻衣起床,趿上了鞋。
“你干啥?”女人的声音很软,温热的鼻息直往他脖子里灌。
“我,给牛添把料!”
福贵知道留在屋里的后果。福贵拿了草料放在牛圈里,蹲在牛圈门口,就着牛津津有味的反刍声,有一口无一口地抽着旱烟。
福贵回到屋里,没有了女人的身影,只有女人弥散在夜空中的幽香。
几声鸡啼,把黑沉沉的夜幕扯开了一条逢。

走的时候,福贵把一匝钞票压在饭桌上,嘟哝着骂了一句粗话。
福贵气汹汹的,不知道在生谁的气。

福喜
知道福喜底细的人,清楚他那两手三脚猫功夫,免不了在背底下嘀嘀咕咕。
对于村里人的质疑,福喜总会涨红着脸,把额头上那几根青筋张牙舞爪地凸显出来,用咄咄逼人的唾沫星子咆哮出他的愤懑:说个屁,老子在城里那半年白学了?

福喜不说这句话,打几个哈哈说不定还可以蒙混过去。恰恰这句话,把他给出卖了。
福喜确实到县城赤脚医生短训班学过。准确地说来,福喜就去了一个礼拜。村里人的见识比眼屎还小,对于礼拜这个玩意儿,把玩了半天也闹不明白是啥意思。还是福喜连比带划,才在脑海里烙下了这个概念。现在,一个礼拜竟然拉长为半年,自然给村里那些认死理的犟牛脑壳落下口实,难有翻盘的机会。
福喜从县城回来,就背上了一个写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小药箱,成了村里人口中的医倌。
福喜最重要的药是止痛片,不管哪个地方疼都用得上,特别是头痛脑热一类的小毛病,这个东西还相当灵验。福喜最擅长的手术,就是拔火罐。用一个小瓦罐,沿口拭上清水,把点着的草纸装进罐里,捂在早已扒光衣服的部位。在旁边人的惊呼中,取下瓦罐找块碎碗的瓷片,往鼓得青紫的地方轻轻一戳,放出几滴污血,风湿劳损类的病情就好了一大半。福喜得了空,也会上山挖些草药,阴虚火旺,跑肚拉稀这样的病症,他都有自己的办法对付。
当然,福喜最为豪壮的还是给病人打针。
福喜只有一把手术钳,一支针具,和一个褐色的瓶子。那只神秘的瓶子装着酒精,专门用来泡那只宝贝针头。每次打了针,福喜就让人烧壶水福贵烟,把针头针管丢进茶壶里,煮上一袋烟工夫,再把针头捞起来泡在酒精瓶里。
福喜给人打针,也要消毒。不过,他舍不得用酒精,每次消毒都用村里的老烧酒代替。棉球当然也是自制的,他家那床厚厚的棉被已经空了一大半,除了绝少数用来做煤油灯的灯芯外,其余的都被他用钳子夹来消毒了。
乡下人难得打针。虽然福喜只用柴胡、鱼腥草一类中草药针剂,但这针扎下去还真的管用。随着打针次数的增多,福喜的名气一天天看涨,说话的声音也一天比一天洪亮。

别看乡下人粗门大嗓,说话做事风风火火。可是,坐在福喜面前的独凳上,犹如上了刑场一般恐怖。在脱裤拧胯的过程中,往往针还没有扎进去,身上的汗毛就已经紧张得立了起来。

所有这一切,对福喜那根宝贝样的独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
表叔就是这样。表叔得了重感冒,在床上躺了三天,还是昏昏沉沉下不了床。表婶揣着一颗怦怦跳的心,把福喜请到了自己家门。
“没得事,打一针就好了!”
福喜朗朗的笑声,犹如一剂定心丸,让一家人悬着的心落了一半。
老躺在床上不是事。大家把表叔扶了起来,让他坐在板凳上,方便福喜操作。可是,福喜才把老烧酒抹在他的屁股上,表叔啊哟一声,身子一下耸起来,倒把大家吓了一大跳。
“不怕,就跟蚂蚁叮了一样!”
福喜乐呵呵地安慰着,矮下身子,手一扬,把针扎了下去。
没想到,唉哟一声,表叔身子又是一耸,接着就是一声惊叫:“扯拐了!(出问题了)”
惊叫声是福喜发出来的。表叔把针头扯脱不说,那根长长的针,也让他别弯了。
“动不得,动不得!”福喜温厚的巴掌赶紧按住表叔的肩膀,大吼道:“你把针弄断在里面,就糟糕了!你晓得不,那是要去县医院开刀才拿得出来的!”
在旁边端着油灯的表婶着急了,在旁边帮着腔:“要不,我找把锥子来,先往屁股上戳个洞,再顺着洞眼打进去嘛!”
“按说是可以的。”福喜把针筒放在桌子上,伸出食指和中指,在表叔那个扭扭捏捏的屁股面前,反复校正了位置,说:“关键是现在针头只进去了一半,外面半截弄弯了!你赶紧找把钢丝钳来,帮忙把针扳直了,将就打一针再说……”
摇曳的油灯下,凝重的呼吸在屋子里跌来撞去。福喜的钳子在下面夹住针头,上面一把钢丝钳在校正。大家用一通热汗作铺垫,总算把这一针给打了下去。
村里有一个叫黄大仙的姑娘,不知道得了一种什么怪病,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年了。黄大仙的父母很着急,请人跳大神送瘟神,家里闹得乌烟瘴气,白白丢了几只老公鸡的性命,损失了几个腊火腿,还是没起作用。
一家人凑了些钱,把姑娘弄去县医院住了一个月,仍然没有效果。对姑娘的病,一家人都丧失了信心。哪天眼睛闭,哪天送上山去,也算尽到了当父母的责任。
只有奶奶不这样看。奶奶从小把丫头带大,就算不要这条老命,也得想办法把孙女的病治好。
奶奶颠着身子,请了福喜去给她看病。家里人都知道福喜那点功夫,连县医院都拿不下来,他要能治好丫头的病,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不管咋说,只能死马当活马医,走一步看一步。

其实,福喜心里也没底。他找草药敷,煎汤水内服,熬制补气健脾除湿去燥的食物进行调理。
姑娘原本白皙的背上,全是福喜拔火罐留下的青淤。一个个错落有致的血印子,就像一只只张着血盆大口的狮子,让人感到无比的恐怖。
都说药医有缘人。经过大半年的调理,黄大仙不仅站了起来,还能慢慢下床走几步了。
到了这年秋天,黄大仙可以出门,抱柴、烧火、喂猪,帮助奶奶做些零碎的家务。
黄大仙一家感激万分,他们没有想到女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。
入冬以后,在南高原暖阳的爱抚下,大家都闲下来。黄家杀了两只羊,把亲朋好友都请过来,好好庆贺这件大好事。那时候,黄大仙已经能下地,帮着干一点轻巧的农活了。
亲友轮番地劝酒,把福喜的脸烧成了阳光暴晒后的瓦片,刺辣辣地泛着热气。
那几年,福喜一门心思帮人治病,家里后院起火。有人不仅给他戴了绿帽子,他的女人留下两个孩子,跟着一个远方的木匠远走高飞了。
要不是福喜,丫头这后半生就只有在床上度过。黄家父母念叨福喜的好,有心让黄大仙跟着福喜过。父母私下问过姑娘,就等找机会把话挑明了。
晚上,黄家在堂屋里烧了一大盆炭火,一大家人围着火盆,用家长里短温暖着岁月的苍凉。嗞嗞飞溅的火星,伴着其乐融融的笑声,脉动着夜的温情。终于,有个老辈人把话题转到福喜和黄大仙身上,揭开了这张底牌。

“嗨,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?”
福喜脑袋晕呼呼的,满脑子是小木匠那张似笑非笑的脸。
“我我我……难道就图这个?”
福喜没头没脑丢下这句话,站起来就往外走。
夜空深邃,天幕上的星星让夜风擦得亮亮的。身后有呜呜的声响,不知道是风声,还是黄家丫头的啜泣。
绘图 瑞筠
投稿邮箱:shishuo@xawb.com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加站长微信免费获取积分,会员只需3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thumbxmw

